艾涤生,《田纳西新闻》及《田纳西华人世界》特约评论员——2018年10月1日生于纳什维尔。骨是对理性的追求,肉是对感性的尊重,表达的是独立的思想,幻化的是洗涤后的重生。为的,是那一束光!
导言
了解田纳西纳什维尔的朋友们一定听说过Centennial Park(世纪公园)。公园中有一座仿古的“帕特农神庙”。它仿照已经被摧毁的古代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按一比一大小建成,庄严肃穆又不失现代感。很多人选择在此处公园草坪上席地而坐与朋友谈笑风生,在这宁静和谐的氛围中感受历史和现代的碰撞。
然而,就在上个月,此处竟然发生了一件令人又惊又悲的“泼墨门”事件。坐落在公园一角的青铜雕像竟被不知名的民众用醒目的大红色油漆泼洒。该雕像是于1909年为纪念南北战争中的阵亡将士所建,已有百年历史。底座石柱侧面上刻着当年战死沙场的老兵名字共计540个。其中一面被猩红的油漆喷上了“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的英文大字,其他几面也被倒灌下来的红漆涂抹得“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这样的“群氓”事件需要我们反思。笔者的分析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为主题,下篇以“政治正确”为主题。本文做为上篇的宗旨是阐明这样一个观点:言论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意见的自由市场是法治框架下的自由市场,以公众利益和道德约束为前提——这种包含道德内涵的法权思想,是超越阶级、党性、历史阶段的普遍思想。笔者将从以下三点来论述以上观点:(1)错综复杂的“南北之争”:从“挡校门”到“邦联旗”;(2)“意见的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把情绪装进法律的牢笼;(3)“依法发怒”和“民怨管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点思考。
(1)
错综复杂的“南北之争”:从“挡校门”到“邦联旗”
在美国短暂的200多年历史篇章中,南北战争和奴隶制的终结是美国历史中最重彩浓墨的一章。尽管如此,美国的“南北问题”却持续至今。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内部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些人主张各州不受到联邦政府的过多干预,从而形成一种较为松散的“邦联制”(confederate)体制。另一些人则主张美国应当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federal)政府,使各州的自主决定权收拢在一个统一的“联邦制”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之间对“要不要联合”、“要不要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仍然难以达成共识,冲突反而日益严峻:北方以资本主义为主,主张废奴,南方以庄园奴隶主经济为主,反对废奴。经济体系的冲突夹杂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为日后南北战争的到来埋下伏笔。1860年,林肯参与总统竞选并获得大胜。支持蓄奴的南方七州面对这一局面,终于忍无可忍,采取激进策略,宣布脱离联邦,组南方“邦联”(the Confederate)。随后,南方邦联军队(或“南方联盟军”)组成,在次年4月12日凌晨炮轰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要塞(Fort Sumter),就此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炮。
然而,这场历时四年、伤亡惨重的内战并没有帮助美国消弭南北之间的深刻冲突。虽然北方人认为内战的胜利是伟大的历史事件,它获得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废除奴隶制的大门,但南方人则坚持着自己一贯的“州权叙事”。他们相信,北方人眼中的内战并非正义之战,所谓的“统一”仅仅是北方军队对历史所作的“胜者为王”的解释——明明是北方军队入侵南方,却把南方各州追求自由和州权的宪法权利谬传为“分裂国家”的行为。甚至有些南方人认为,“废除奴隶制”本质上是对“侵犯奴隶主财产权”之暴行的一种光面堂皇的包装。有的南方蓄奴理论家还提出,杰佛逊主张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不平等是自然和社会的本性,只不过上等人和奴隶主怀有慈善义务,愿意本着良心和仁慈的心意去关怀“下等阶级”而已。
另外,奴隶制从它的诞生初始就与“种族主义”紧紧相连——它是“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奴隶”的奴役。内战虽然从政治制度上废除了奴隶制,却未能从南方人的内心中废除奴隶制;而留在人们内心中的奴隶制,还融合着种族主义的色彩——尽管美国黑人被赋予了平等的宪法权利,但黑白隔离的政策却仍然在内战结束后大行其道。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间,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了将近一百年之久,南方各州仍然有顽固不化的势力宣称黑人不配与白人一起吃饭、坐车、受教育。在很多南方白人心目中,“他们黑人”——因为与“我们白人”具有不同肤色——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二等公民。
电影《阿甘正传》中有这样一段经典演绎取材于真实的“阿拉巴马州长挡校门”事件,影片中由汤姆·汉克斯演绎的阿甘亲身参与了两名黑人学生被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录取后的注册过程。该事件浓缩反映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州权对抗联邦权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1954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布朗败诉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委员会案(即,著名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确立了公立学校采取种族隔离制度乃违宪行为。1963年6月初,阿拉巴马州所属的联邦法庭正式判决,命令阿拉巴马大学必须承认三名黑人学生的入学资格,并禁止州长乔治·华莱士阻止他们入学。然而,华莱士州长决意阻止非裔学生入校,并竟然“以身挡人”,生生堵在学校礼堂门口拦住前去注册的学生。由肯尼迪总统派去的司法部长助理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见到“人墙”华莱士后叫他“靠边站”,华莱士纹丝不动,并开始发表一通有关州权的演说。亨利·格兰姆将军率领四名法警上前对华莱士说,“先生,在合众国总统的命令下,我有这个不情之请,请你现在就退下。”华莱士仍然僵持不退,一直到自己的州权演讲结束后,才让开了入口的位置,让两名非裔学生进入礼堂注册。
尽管距离“挡校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种族问题和州权问题的微妙联系却从来没有从公众生活中淡去,甚至出现了越演越烈的趋势。近几年来,“邦联旗”是另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标志。南北战中期间,邦联军使用过一面带有蓝色嵌星十字叉的红颜色旗帜,又称反叛旗或南十字架旗(southern cross)。该旗帜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就被禁止悬挂,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又逐渐重登舞台,多次在重大活动和公共场合公开亮相。许多在南北战中为了保卫自己家园而战死的邦联老兵们,他们的后裔常在纪念仪式上使用这面旗帜,视之为“先辈的光荣象征”。但同时,也有些人利用邦联旗来宣传种族隔离和白人至上主义。有不少所谓的“保守主义”或“南方传统”实则是对封建、落后思想的宣传,如女性必须从属家庭等。令人痛心的是,2015年,一名佩戴邦联旗帜印章的枪手DylannRoof在南卡Charleston市一家黑人教堂中扫射,打死9人。这起枪击事件一夜之间引发激烈辩论,许多美国人走上街头,呼吁在公共场合淡化邦联标志。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泼墨门”事件的成因了:泼墨者相信,邦联标志归根到底表达的还是对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的宣扬。但是,邦联标志的拥护者们则认为,联邦旗帜是历史文物,蓄奴历史也是美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废除联邦旗或禁止联邦标志的公开展示联邦政府对南方文化的迫害。而且,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宪法权利,认同南方价值和文化传统的美国公民享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无论上述两种态度哪一种是正确的,恐怕我们多数人都会同意,泼墨者公然破坏历史文物的行为是粗暴的,也是违法的。事发以后,纳什维尔当地警局立刻调取公园周围的摄像记录来追捕嫌犯,而大部分本地居民和新闻媒体也对这种毁坏公物的行为进行了道义谴责。
也许有人会说,“泼墨门”只是一群小孩率性而为的嬉闹,一次不懂事的任性,不值得“小题大做”进入政治学的讨论。对此评论,笔者的回答是:毁坏公物的行为不是“率性而为”这样轻描淡写的描述就能一笔带过,无情的法律也不会对此“孩童的任性”网开一面。文明社会的人们应该要意识到,“意见的自由市场”并非彻底自由。从未享受过抗议权利的良民们渴望着暴动的自由,而自由世界中的暴民们则需要秩序的约束。
(2)
“意见的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把情绪装进法律的牢笼
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定充满着无数开放的命题态度。南北战争、蓄奴主义、种族平等,都是成千上万个“开放式命题”中的一个。就算已经手握真理,我们也不能忘了:知识的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所争论、质疑、反复,甚至是反动,都是正常的现象。我们的意见并非一夜之间就能形成,而是往往需要反复衡量、消化和体会才逐渐巩固起来。想要改变人们的固定思想,一个教育者不仅需要知识和立场,还需要有沟通的艺术。
以亲子关系为例,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对话关系是亲密的、友善的,那么分歧和摩擦通常能获得彼此的谅解,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当教育脱离了亲密的家庭关系,走向了社会平台,触及了政治的话题,“教育者们”和“被教育者们”就都站上了一个更错综复杂、彼此隔离的“公共舞台”。从此,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而亲密的个体关系,而是被一张看不见的、抽象的“政治之网”所缠绕。原本温情脉脉的“爱与辜负的话语”在经过了社会化、政治化的重构之后,被转化成了冷冰冰的“权利与压迫的话语”。这种转变为人民的对话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有些人可能会打断笔者说,难道愤怒本身不就是一种正当的道德情感吗?难道愤怒的抗议不正反映了“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怀吗?难道不正是“被愤怒”的对象——即我们的社会、受批判的群体——需要去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吗?当然,就其积极的方面来说,激烈的愤怒确实是一种迅速起效的情感惩罚,能当时当刻令对方感到震动,唤起对方心中的羞耻感和愧疚感。群体性的愤怒行为,如抗议、游行、打砸抢、破坏公物等,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表演”的行为。这种表演能一瞬间迅速抵达社会各界,用触目惊心的方式起到直接、深入和广泛的公众影响力。无论是抗议、示威、游行,还是毁坏公物的行为,在愤怒者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目标历史实现之后,后人也往往会肯定它们在当时的特定条件起到的社会意义。
但我们也要想一想,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中,比起暴力抗议的领袖,“非暴力抗议”的倡导者们才具有更高的历史地位和领袖价值?表达正当愤怒的民权运动家如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者,宁愿依法上诉、牢底坐穿,也不拿起武器上街杀戮。因为他们知道想要真正改变美国的种族不平等事实,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把诉讼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在全国人民面前用法律的武器和宪法的语言来辩护自己的权利。愤怒的情感虽然强烈有效,但同时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在文明社会,抗议的权利不是无条件的最高权利,而是必须依法申请、依法抗议,在获得许可的区域里,用干净卫生、和平有序的方式展开。这些法律的约束,并不是要人压抑内心的不满,而是要人把内心的不满用和平和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博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但是,如果人们脱离了谦逊克己、宽容异己的原则,让自己的内心认知从“你对我错”上升到“你无知我有知”、甚至“你低劣我高尚”的结论,那么求同存异、和平沟通的道路就更难了。事实上,最深刻的宽容恰生长于最深刻的分歧,越严重的分歧也越需要宽容的智慧。真正撕裂社会的从来不是观点的分歧,而是发表观点者的敌意和傲慢。正因如此,自由言论的权利从来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我们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必须接受公共秩序和公众利益的约束,从而使得多元冲突的思想不以粗鲁暴力的谩骂方式呈现,而以彼此切磋、彼此商讨、追求真理的和平对话展开,这样才能最终成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超越格局。好的教育不应该只有义愤填膺的谴责,还应该有体面的循循善诱。体面的政治表达,应当懂得把情绪装进法律的牢笼,而不是让知识的传播背负着傲慢的包袱。
(3)
“依法发怒”和“民怨管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点思考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笔者上述这套说法不过是在给美国大唱赞歌。其实“泼墨门”事件很简答,无外乎反映了美国内部深刻的民族矛盾,以及各州不服联邦的国家危机。而把泼墨者绳之以法的现象也很简答,无外乎体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阶级意志而对被统治阶级强行施加的压迫罢了。比如,美国的婚姻法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冷冰冰的利益争夺;同样,所谓“言论自由的法制边界”,也不过就是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特殊喜好强迫全社会共同承认一套他们自己的标准,是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对另一部分无权无势的弱者进行压迫的手段。
上述阶级分析法在有些情况下确实有其尖锐独到之处。古今中西的人类历史中,我们看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对于个人基于良心所选择的信仰和思想,凡是当局认为有害的,就会出现法律以全体公民和正义的名义宣布为反动的、邪恶的、别有用心的。人民想说什么,需要经过统治者的批准。因为人民想说的话太多了,比如,既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恶意的攻击,既有统治者想听的,也有统治者不想听的。于是,统治者首先要界定言论的善意性和恶意性,并把这种界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配上相应的奖惩机制,从而实现驭民的目的。一句话,统治者想要奴役人民,就说人民不懂把情绪装进法律的牢笼,而一旦想要利用人民,就鼓励人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而“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
但是,如果这种阶级分析法被当做了理解“法的本质”的“万精油”,却又过于狭隘、以偏概全,缺乏充足的理论解释力。这是因为它无法解释两个重要现象:(1)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法可以不断自我修正,以及(2)为什么立法者本身也要服从法律、“依法立法”、“依法废法”、“依法释法”。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从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开始说起:
首先,任何社会合作都需要稳定的秩序,这乃是由人类这种动物天生的特性所决定——单凭个体的力量,我们既无法抗拒自然世界的原始力量,也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物质资源来满足生存之外的需要。然而,任何合作都会出现分歧,这也是由人类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我们的天赋和才能、需求和目的各不相同,有限的物质资源和无限的人类意志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必须迅速地裁决分歧来保障稳定的合作。无论这种裁决是多么地仓促和不完美,人类社会的这艘航船必须首先开始启航,驶向大海。不然的话,它就只能永远因为分歧和“窝里斗”而停在港口,而我们人类也永远只能沦为自然的奴隶,无法用凝聚的社会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才能。
因此,有鉴于一个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无能,有鉴于一个人在合作中必然体现的丰富个性和有限资源,并最终有鉴于人类有自我保存、繁荣发展的强大愿景和对受自然奴役、彼此争斗之苦的深刻恐惧,全体人类必须迈出了通向文明的步伐,即,放弃自己作为原始人所拥有的野蛮的、暴力的、自然的平等,用法律的、道德的、社会的平等来缔结一份神圣的社会的契约——这份社会的契约以法律的名义剥夺了每个人“自然的自由”,却交付了他们“社会的自由”。从此,“自由”被赋予了“依法”和“自律”的内涵,而不再是“放任”的“强力”。
然而,这份神圣的“社会的契约”,是人类的契约——它注定是不完美的。然而,我们必须接受这种不完美——人类社会这艘巨轮既不是尚在草稿纸上的伟大构想,也不是已经抵达港湾结束行程的完美造物,而是正在汪洋大海中迎着风暴、时有漏水,却为了继续航行而不得不自我更新、自我纠错的“破船”。反过来说,之所以“一艘破船”还能航行,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令人惊讶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
一份理想的社会契约,它所应当具备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规定该社会自己如何“自我修复的条约”——如何“依法执法”“依法立法”、“依法修法”、“依法废法”、“依法释法”的根本大法,即,拥有一部合法性来源于全体人民、形式和内容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宪法。
尽管社会契约论和宪政民主政体的内在关系不是这里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但是我们至少要学会观察如下两个社会现象:
第一,一个国家中的恶法或所谓“以私意裹挟法律”的现象到底是被普遍地贯彻在它的根本大法和政治制度——即宪法和政体的层面上,还是仅仅体现在个别的、地方的政治操作和集团利益中。
考虑到风俗民情未必合理、人类理性常常犯错,故掌握权力和资源的阶层常常用自己的意志操控无权无势的民众,这是任何人类社会都无法避免的。然而,统治阶级利用法律并不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人民没有法律的武器去制裁统治阶级对法律的践踏。
有心为美国唱赞歌的读者们,可能会在这里不禁欢呼:美国之所以强大,其中一个原因不正是在于她的社会制度赋予了每个公民以批判统治者的权利吗?以法庭上的较量来说,民告官胜诉、政府机构被判决赔偿公民百万美元的案例数不胜数。“泼墨门”作为一个反应某些公民表达自身政见而被法律制裁的独立事件,并不改变美国社会整体对言论自由——尤其是民告官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依法抗议的自由——的法律保障。
一个理想的社会,它的法律保障是面对所有公民的——担任公职者和普通公民、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投资者和劳动者、有产者和无产者,总之一切被称之为本国公民的人都在他们的宪政体制下享有平等的地位。一个宪政治理下的法律体系,是无法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去解释的。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无差别”(difference)的社会,而只是一个“无凌驾”(domination)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虽然有掌握不同社会资源的“社会阶层”(social stratum),却没有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一方凌驾另一方的“社会阶级”(class)。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是所有公民——不管他们来自什么阶层——一起平等地分享着政治权力、平等地被赋予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约束。占据公职的行政官员和掌握更多经济资源的精英阶层,他们只是人民委托的办事员和公共财富的保管者而已。他们既不是这艘社会大船的发动机,也不是领航人,反而是整套纠错机制的监督对象。卢梭洋洋洒洒几万言,不过就在此一句话。
第二,我们还要考察,我们的人类社会这艘仓促启航的“破船”,如果它还有幸依靠着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大海中航行的话,它的自我修复机制到底是自下而上、一视同仁的民主问责监督制,还是靠统治阶级自己“内圣外王”之道德自觉的自我监督制?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挡校门”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了全国讲话。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肯尼迪总统对全国人民说:“从林肯解放奴隶以来,10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依然没有得到全面的自由,我们已经推迟了100年。他们还没有从各种不公正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还没有从社会和经济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个国家,尽管有诸多希望和荣耀,但是在所有公民获得自由之前,都不是真正自由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统,如果是代表自己的人民说话,他就会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以人民所受的苦为自己所受的苦,以人民所追求的自由为自己所追求的自由。所以,他就会主动承认自己的国家不够自由,不够公正,不够强大。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不“先天下之忧而忧”,就会连听到人民“善意的批评”、乃至被人民“唱衰抹黑”的机会都没有。只有朝鲜才永远昌平盛世、皇恩浩荡,才挤满了“小骂大帮忙”的权臣、“敢怒不敢言”的人民和“跪求赏民主”的奴才。实际上,人类历史的经验无数次地告诉我们,从来不是因为社会中存在某些不合理的法律和某个不尽职的统治阶级而导致国家的倒掉——只有当人们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得进行报道,当一颗“独夫之心”不可受到批判,当所有仁人志士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心情才能自由地说话时,我们才会懂得这句话的意义:“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些扯远了,那就赶紧打住吧。
总结
综上所述,笔者希望本文已经清晰地论证了这样的观点:首先,言论自由有它的边界,对公共福祉的考量要求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在法律框架里表达意见,“依法发怒”、“文明发怒”。而令国家陷入危机的并不是恶法、民怨和腐败,而是对这些社会的不公无人敢说、无人能改;反过来说,越是在一个自由的制度下生活的人民,他们就应当越有充分的自由表达不满,就越不会随随便便“逼上梁山”。其次,从法理学的高度来看,法的道德内涵是普遍的,它以守护所有公民的公共福祉、共同繁荣和政治平等为目标。这一目标构成了所有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政体的根本内核,是人类政治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结晶。如果我们对法的本质的理解被“到底是黑猫还是白猫”的二元对立所主宰,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拿来主义”勇气,错过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中的政治文明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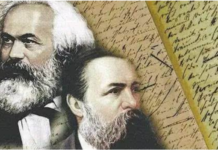
 《田纳西新闻》在建报之初一度是是田纳西州唯一的华文周报,总发行量最高超过一万份。近年来,《田纳西新闻》改为以网络为主,打造了《田纳西华人世界》微信平台, 继续为广大华人服务。本报以公平, 正义, 和平, 友爱为原则, 不带任何种族, 宗教, 政治偏见,竭诚为本地华人提供美国和当地的时事新闻和文化咨询。我们欢迎各类广告,有意者请拨打电话(615)977-8582。
《田纳西新闻》在建报之初一度是是田纳西州唯一的华文周报,总发行量最高超过一万份。近年来,《田纳西新闻》改为以网络为主,打造了《田纳西华人世界》微信平台, 继续为广大华人服务。本报以公平, 正义, 和平, 友爱为原则, 不带任何种族, 宗教, 政治偏见,竭诚为本地华人提供美国和当地的时事新闻和文化咨询。我们欢迎各类广告,有意者请拨打电话(615)977-8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