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特朗普总统定点击杀苏莱曼尼一事再次激发了两党的一个重要争论,即美国总统究竟凭什么享有合法权利对威胁美国安全的境外势力成员实施击杀?不少民主党人士站出来质问特朗普:“即使苏莱曼尼是美国的‘头号敌人’,难道就可以完全绕开国会决议、任凭总统一个人的意志想杀就杀吗?”当然,在这个质问背后,还存在另一个更实质性的担忧,即,做为伊朗第二号头面人物的苏莱曼尼,他这样突然暴毙于美军之手,难道不会引起掀然大波、促发大规模的区域战争吗?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总统的“擅自行动”是否存在滥用权力而应该被限制?这样的话,总统如此行事到底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呢?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纽约的民主党议员艾略特·恩格尔(Eliot Engel)说,“这场刺杀行动没有经过国会决议,有着严重的法律问题,挑战了国会作为一支独立政府部门而存在的地位。法律要求相应的通知步骤,这样总统就不能冒然地把美国拖进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中去。”
共和党中也有一些成员对特朗普的行动表示担忧,对总统是否能单方面宣布刺杀苏莱曼尼持保留意见。2001年国会出台了AUMF法案(Authorization to Use Military Force,即军事力量使用授权法),赋予总统以使用武力打击任何与911袭击相关地域或人员的权利。2002年国会又接着出台了2002 AUMF法案,其中批准了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尽管这两次授权法案的出台是在本世纪初,但它们到今天仍然有效。
但是,据外媒采访的柏克莱大学法学教授John Yoo(约翰·柳)分析,AUMF法案赋予了特朗普总统本次击杀苏莱曼尼的合法权力。不过,即使该法案并没有赋予总统该项权力(比如该法案被国会宣布废除),美国宪法本身也已经赋予了这样的权力。
本报记者特此采访了纳什维尔王氏律师事务所的Vivien Wang律师,王律师分析了美国宪法及法规对总统和国会权力的规定,希望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次击杀事件背后的法律依据。

(1)-
总统宣战权的宪法基础
首先,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美国国防安全、国家福祉,国会有权宣战。接下来,宪法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进一步规定美国总统为美国军队和海军总司令(Commander in Chief),从而赋予了总统一种默许的特权(implied privilege)来发动对外战争。
但是,长久以来,美国总统这一默许的、特殊的军事权力却构成了美国宪法学界和国家宪政实践中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建国者尽管赋予美国总统这样的特殊权力,但却同时加以种种约束,以使战争手段的采用被保守地使用于防御性行动中,而不至于因为挑起敌意而将美国卷入“战争行动”(hostilities: acts of warfare)。基于这样的保守主义和权力制衡的考量,美国总统在对外宣布发起军事进攻之前多半要首先经过国会的同意。因此,自1789年来,国会一共对10个国家宣战11次,每次总统都向国会申请授权批准,无论是通过个人当面申请还是提交书面申请。
但是,这一保守主义倾向在二战以后逐渐瓦解。尤其是911公布袭击以后,布什政府治下的国会接连颁布了两份AUMF法案(2001法案和2002法案),奠定了被许多人批评为“使总统总揽对外宣战权”(granting President sweeping authority)的法律依据。该法案用含义模糊但语气明确的语言授权总统宣战权,只要总统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国际和平和和地区安全”。
(2)
1973年战争权力解决法案
第二,与这一保守主义趋势并进同行的还有另一项重要的联邦法案,即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解决法》(War Power Resolution,或War Power Act)。该法案旨在制衡总统绕开国会而自行宣布对外军事行动的权力。具体来说,总统如果要派兵前往国外进行军事行动的话,那么这一行动要么是本身已经经过国会授权和宣布而具备合法依据,要么是因为美国国土受到他国攻击而陷入严峻状况下被紧急发动。
如果是后一种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总统未能及时经由国会授权和宣布战争而率先自行派遣军事力量,那么总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在行动之后的48小时内通知国会。不仅如此,由于该军事行动未能经过国会的事先授权和正式宣告,行动时间不得超过60天。一旦到了60天的行动期限后,如果国会仍然不同意该次行动或拒绝正式宣布对外站长,那么总统必须要求军队在30天内撤离该军事打击目标国。
根据外媒的报道,在本次特朗普击毙苏莱曼尼事件中,白宫确实在1月4日合规地正式通知了国会,告知总统已经在前一天下令击杀苏莱曼尼。白宫坚称,总统的行为严格遵循了《战争权力解决法》和2001年的AUMF法案。如果白宫确实按照法律通知了国会,那么近几日来民主党议员们对特朗普的重重质疑声就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了。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无论特朗普做什么样的决定,民主党人都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在野党对执政党“鸡蛋里挑骨头”,乃是天天上演的“美国政治日常”。1月9日,国会如约就白宫在1月4日对伊行动一事以224:194的投票决定限制特朗普在没有国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不过,这个结果应该既不令特朗普沮丧,也不令民主党雀跃。毕竟特朗普就伊朗袭击一事发表的全国讲话中的信息已经相当清晰,他本来就没有意图让军事事态升级,而其击杀苏莱曼尼的目的也已圆满完成。
不过,作为关心美国政治的朋友们,也不妨借这个机会对美国总统宣战权背后的历史和法理做一番考察。
(3)
民主党总统对宣战权的使用
2013年,奥巴马向国会提出授权要求以便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国会拒绝授权。不仅如此,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提案,其中一条有关“战争行动”(hostilities: acts of warfare)的条款被视为专门用来限制总统和国防部长在军事行动上的决定权。该条款表明,如果环境和局势能够明显证明该地区存在“战争行动”升级的情况,那么无论是总统还是国防部都没有当然的法定权利派遣美军前往该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然而,奥巴马完全无视于该条款的禁令,下令美军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使美国成为了第一个全面进驻该国的西方国家。
奥巴马绝不是第一个无视国会法令的总统。1999年,克林顿总统就已经按照1973年《战争权力解决法》的规定,在未经国会授权批准的前提下向科索沃发动空袭。尽管按照法律在规定时间内通知了国会该行动,但这场空袭在60天的法定战争期限到期之后持续了两周之久。面对逾期未撤的指责,克林顿的法律团队却强词夺理地争辩道,这种行为是合情合理的,符合战争权力解决法规定的,因为国会在得到空袭通知以后批准了总统的军费申请。既然国会给行动拨款,那就意味着国会事实上认可了总统的决定。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克林顿所说的那样。《战争权力解决法》写得很清楚,同意军费拨款并不等同于批准总统发动军事行动的要求。因此,克林顿的科索沃行动被33名国会议员联名告上了法庭,带头人为来自加州的汤姆·坎贝尔议员(Tom Campbell)。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巡回法庭受理了该诉讼,起诉理由是克林顿的行动既违反了宪法又违反了《战争权力解决法》。然而,法院最终以“政治问题不应由法庭来判决”为由判决该起诉不成立。原告不服判决后上诉,然而上诉庭维持原判,理由是既然国会之前已经有了大量的立法空间来左右总统的军事决定,那么国会就不能再通过法院这条司法途径来干预国家的行政机构。
不知道当今天民主党人拼命攻击特朗普击杀苏莱曼尼一事的时候,是否有回想起来以上这两位“自己人”所做的相同行为?
(4)
权力制衡的老问题
当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中的谁发起军事行动,我们似乎都必须承认,之所以近现代以来美国总统绕开国会、钻法律空子而发起军事行动的权力逐渐扩大,并非仅仅是政客滥用权力那么简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瞬息万变,国家利益当前采取迅速举措便刻不容缓。总统既是保卫国家利益的行政长官,又肩负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责任,而国家和公民的福祉都不可能脱离整个地球村上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存在。因此,美国总统确实存在着发动紧急军事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理由。
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总统的任何行为都要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监督和制衡,不能任性而为。根据分权制衡、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统和国会各自发动战争的权限边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宪法初衷来看,由国会而不是由总统个人做出发动战争的决定会更为稳妥和安全。但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面前,宪法设立所捍卫的初衷有时不得不按照现实情况进行调整。当然,不管怎样,由于美国是一个讲求人权和民主的国家,在战争这样的重大决定上,可能由国会重新审视现行的相关授权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似乎迫在眉睫的两党现实矛盾来看,在同一部立法框架下相互指责对方与自己采取相同行动时的合法性问题似乎太过没有意义。而可能重新回归国会,立足于宪法并同时重新审视、修改甚至撤销相关授权法才是最有意义的手段。然而,现实中这种情况尚未发生,其中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考虑到了战时紧急时期高效率的对应才是当务之急,因为毕竟总统一人做出的行政命令要远远快于几百人国会开大会才能做出决定。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只有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宪政国家,其桩桩件件大大小小的事务才能被如同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下般地进行审视和辩论。相比于那些完全在秘密通道中公开出来的其他国家首脑行政命令,克林顿、奥巴马也好,特朗普也罢,谁都不是暴君,更不是独裁者,而可能仅仅是被反复暴晒的“可怜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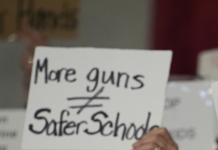
 《田纳西新闻》在建报之初一度是是田纳西州唯一的华文周报,总发行量最高超过一万份。近年来,《田纳西新闻》改为以网络为主,打造了《田纳西华人世界》微信平台, 继续为广大华人服务。本报以公平, 正义, 和平, 友爱为原则, 不带任何种族, 宗教, 政治偏见,竭诚为本地华人提供美国和当地的时事新闻和文化咨询。我们欢迎各类广告,有意者请拨打电话(615)977-8582。
《田纳西新闻》在建报之初一度是是田纳西州唯一的华文周报,总发行量最高超过一万份。近年来,《田纳西新闻》改为以网络为主,打造了《田纳西华人世界》微信平台, 继续为广大华人服务。本报以公平, 正义, 和平, 友爱为原则, 不带任何种族, 宗教, 政治偏见,竭诚为本地华人提供美国和当地的时事新闻和文化咨询。我们欢迎各类广告,有意者请拨打电话(615)977-85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