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涤生,《田纳西新闻》及《田纳西华人世界》特约评论员——2018年10月1日生于纳什维尔。骨是对理性的追求,肉是对感性的尊重,表达的是独立的思想,幻化的是洗涤后的重生。为的,是那一束光!
一、案发经过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2日13时14分,59岁的贾迈勒·卡舒吉(JamalAhmad Khashoggi)走入了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总领事馆。他36岁的未婚妻简吉兹(HaticeCengiz)在领事馆门外等候。在苦等几个小时还不见卡舒吉出来后,她随即报警。四天之后,两名土耳其官员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卡舒吉在进入领事馆不久后就遭到杀害;另有卫报获得消息称卡舒吉遇害后已另遭遗体转移。沙特立刻以“毫无根据”为由驳斥了媒体的说法。
然而,10月17日土耳其方面披露了重要的录音证据:卡舒吉在进入领事馆不久后,他的手指就先被斩断,之后头又被割了下来。虽然全程仅仅只有7分钟,但卡舒吉的惊天惨叫证明了他的死亡是基于残忍虐杀,甚至是活体肢解。在录音中能够听到一个被称呼为“医生”的人劝其他人在他对卡舒吉进行肢解的时候带上耳机听音乐。(据悉,这位医生名叫穆罕默德·图拜吉(Salah Muhammed ATubaigy),是一名法医,他在入境土耳其的时候携带了一把骨锯。)
经过多日否认和辩解,直到10月31日,沙方才首度公开正式承认卡舒吉之死是“有预谋”的,他是一进入领事馆就被勒死和肢解的。11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上述这些录音证据已经交给了沙特、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表明,沙特王室——尤其是沙特王储穆罕穆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与卡舒吉的遇害存在某种联系。《纽约时报》早11月12日引用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当日出现在沙特领事馆的特工成员穆特拉比(MaherAbdulaziz M. Mutreb)曾经7次打电话到王储的私人办公室,并在卡舒吉遇害后不久拨打了一通电话,说“告诉你的老板”,任务已经完成了。据《纽约时报》一个月以前的报道,穆特拉比是沙特王储今年访问西班牙、法国和美国时的贴身保镖。
另外,据英国独立媒体《中东之眼》引述消息人士的情报称,沙特派出的暗杀小组在卡舒吉活着的时候,活生生斩下其多根手指,之后将手指当做战利品带回沙特交给萨勒曼王储。消息人士还称,“王储常说,他会砍断批评他的作家的每一根手指。”
距离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已经一个多月了。截止到今天为止,围绕着其遇害过程和尸体下落的具体信息仍然扑朔迷离。10月20日,沙特检方称卡舒吉的尸体因被交给“当地合作伙伴”处理而下落不明;而11月10日,土耳其媒体则称其调查人员在总领事管的下水道中发现氢氟酸和其他强化学物质的残留,推测很有可能是卡舒吉遇害后尸体被强酸溶解化为“液体”从下水道冲走。这一推测吻合了此前土耳其官员所证实的一个重要相关事实:在18名涉嫌参与杀害卡舒吉的特工中,有两名分别是化学专家和毒理专家。
卡舒吉可谓是出身名门,与沙特王室有长期密切的交往,掌握许多王室内幕消息。但他明确地反对萨勒曼王储,是王储诸多反对者中分量最重的一位异议者。在移居美国拥有自由发声的空间后,他成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所发表的文章有至少一半都是在批判沙特王储或沙特政策。在失踪前三天,卡舒吉对BBC的记者说,“被抓进监狱的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异议人士,只不过是会独立思考而已。”他生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做《王储必须结束残酷的也门内战,来恢复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尊严》。
二、国际视野中的沙特人权状况
“杀人灭口”这件事,也许在现代世界也并不新鲜。但是沙特所选择的谋杀方式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砍断手指以警示任何批判当局的作家,派遣庞大的特工团队实施活体肢解,运用现代科学高效神速地溶尸灭迹,其肆无忌惮、惨无人道的杀人方式,震惊国际社会。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大多数人恐怕都不相信这种野蛮行为是任何现代文明国家都能容忍的,但当我们得知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沙特的时候,却隐隐地可能有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感慨。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沙特凭借自己石油大国的地位,早已步入了挥金如土的土豪国家行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频频了解到这片神秘的中东国土仍然有着十分保守落后的社会制度。在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讨论死刑是否应该取消、拘禁在监狱中的犯人是否仍应当享有某些政治权利(比如投票权)的时候,沙特政府还在继续公然无视本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随意抓捕和虐杀王室反对派和权力竞争者。不要说平民百姓,就连王室反对者的财产都经常被粗暴地收缴一空。
然而,先不说其他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利,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女性都已经和男性享有基本相当的权利,甚至许多国家都已经进入到对LGBT权利的讨论中去的时候,沙特的女性才刚刚进入终于被允许看电影和开车的阶段。据维基百科的词条解释,沙特女性仍然不能和男性一样获得银行贷款、出席法庭前必须要先获得来自男性的书面许可、同样的法庭证词两名女性所提供的效力等同于一名男性的效力。仅就由著名的皮尤调查中心提供的分析来看,在整个中东地区,除了沙特以外,其他国家的女性都能够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服装、裸露面部肌肤。而63%的沙特女性只能露出两只眼睛,还有11%的女性甚至必须遮住自己的整张面孔,连眼睛都不能露出。在较为开放和接近主流文明的黎巴嫩、土耳其和突尼斯,都有50%或以上的女性能够露出整张脸,并较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审美偏好来选择头巾的颜色,甚至不带头巾。
另外,由于沙特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神权国家,只有伊斯兰教才能被合法地信奉和实践,其他宗教成员都遭受着极端的压迫。在沙特有将近100万基督教(外加佛教和印度教信徒)。他们大多数是在沙特工作的外国劳工,只能在家中进行私人性的非公开祷告。即使这样,沙特的宗教警察仍然经常定期搜查这些信徒的住所,并且严令禁止类似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宗教庆祝活动。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至今为止,沙特法律仍然规定,从伊斯兰教转信其他宗教可以被判死刑,无神论者被司法认定为恐怖主义者,而任何敢于对伊斯兰教根本原则进行质疑的外国人和沙特公民,都可判最高监禁20年。
当然,当今在位的萨勒曼王储是以一种改革派的姿态出现的。他积极推行新政,尤其是他推动世俗化的各种政策广受国内底层民众和年轻人欢迎。但是,王储的其他政策和打击权贵的反腐行动收效不明显,还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使他承受颇多压力。更令人感到堪忧的是,沙特王室和政府处理批判性言论和打压异己的方式仍然具有相当专制和暴力的特征。今年8月沙特对加拿大外交部要求立即释放维权人士的官方声明所做的激烈反应,恰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了沙特政府的集权特征:
沙玛尔·巴达维(Samar Badawi)和拉伊夫·巴达维(RaifBadawi)是兄妹二人,两人都在为推动沙特的现代化而努力。沙马尔致力于批判伊斯兰教中对女性缺乏自主权和独立人格而必须依靠“男性监护”的立场,主张女性获得投票权,于2012年在美国获得了“国际妇女勇气奖”。
而她的哥哥拉伊夫则致力于取消政教合一,反对宗教立国。他早在2012年就被捕,并被判10年有期徒刑和1000下鞭刑(分20周执行)。加拿大政府在推特上呼吁沙特政府尽快释放这两位维权人士。然而这件事则一下子触怒了沙特政府,沙方一夜之间果断终止和加拿大的通航,并下令让所有留学生尽快离开加拿大回国。沙方还终止了医疗合作,甚至不惜代价抛售加拿大股票债券现金等一切资产。动静之大,速度之快,令人匪夷所思。
三、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伪命题,三个错误点
作为一个挥金如土“物质相当文明”的富豪国家,为何其精神文明程度却如此落后?我们中国人的古话说,“仓禀实而知礼节”。物质基础上去了,精神文明就会跟着发展,这样的自然规律为何没有在沙特发生?
一个错误的问题,注定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它的演变观点“经济发展能带来政治文明”,正是上述这个问题的根本前提假设。然而,这个假设本身有着严重问题,从而导致了预测和评价一个社会的政治变革往往遗憾地建立在一个伪命题之上。
首先,“物质基础”这一概念,如果要全面展开,就意味着一系列相关的权利问题,因而与“政治文明”有着交错的复杂关系。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财富积累,还同时包括了一系列对生产方式、市场交易进行规范与约束等公权力行为模式的发展。事实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这一所谓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经济决定论,或者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已经有了大量的反思和批判。出于本文的目的,笔者只需要指出:即使是暂时不谈及经济发展概念所蕴含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以及人民幸福指数等方面的问题,仅仅是以“物质生产”来理解的经济活动,也至少涉及了生产资料由谁来控制和规范交易活动、生产的参与资格为何、经济活动的盈亏责任由谁来消受和承担、生产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如何界定、审判和处罚等等问题。
第二,不断变化的技术能力、文化条件以及新增的人类需求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并不存在一种“铁的规律”来导致某一种社会形态的必然到来。认真对待和承认这一事实,是历史给人类的教训——有些人想要用武器和流血的力量来强行推动某个历史阶段的“必然到来”,从而枉顾武器和流血在人民身上划出来的伤口;也有些人想要用“必然到来”的借口让人们放弃抗争的机会,让批判现实和反抗暴政的力量犬儒地服从于某些先知式的说辞——这两种极端的立场都在使社会无法鼓励培育那些冷静分析局势和讨论最佳社会变革策略的头脑,使人民要么陷入狂热,要么坐以待毙。
第三,政治文明的发展需要诸多历史经验条件。纯属偶然的不幸事件、外忧内患的政治环境、病入膏肓的政府体系、长期落后的社会传统、压抑禁言的民间社会,许许多多或大或小的现实因素都可能对政治文明的发展造成阻碍。反过来说,即使一个国家的物质发展水平相对充分、没有内忧外患之虑,甚至已经相对现代和开放,但是,即使在诸多有利条件下,她却仍然未必能顺势充分地开创出优越的政治文明,种种或大或小的困难仍可能阻碍这一天的到来——这是因为政治文明的发展不仅要以基本生存条件和社会稳定来保障,以及广泛民主意识和法治权利的维护,更需要第三个更高的条件,那就是,民间社会中存在一个不受威胁的、理性健全的民间舆论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自律而负责的知识分子或精英群体才能和具有公民意识和公共责任感的社会成员进入理性沟通与合作。而这种理性而自由的民间舆论空间的出现,需要经过长期耐心培育的社会土壤。因此,塑造这种舆论空间甚至可能比签发一部宪法更难——在有些国家,宪法也只是少数当权者的政治工具而已,朝令夕改、任意决定,也只是小圈子里若干个“任贤任能”之人的“圣明决断”罢了。
值得强调的是,民间舆论的理性风气不仅无法在短时间里突然成长起来,恰恰相反,却很可能在暴虐施政中被一夜摧毁。面对集权暴政的压迫,底层人民的对抗力量往往是十分有限的。费时数年建立的理性风气,可能在一纸禁令或若干国家暴力压迫中就噤声不语了。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说,历史已经证明了“人民的勇气”是巨大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测试勇气和触碰底线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常态。越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越不需要抛家弃子舍己为人,也越不存在英雄般牺牲的需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读者们都知道,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经常出现的两个主题就是“知识分子的苦难担当”和“朝廷之外的游侠精神”。然而,这两个主题的共同前提,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以及腐朽不堪的政府。试想,如果在一个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被法律保障的社会,如果有一个惩戒分明的政府,如果有一个公平安全的市场规范,那么,我们就能超越圣人与小人的分界,从而接近彼此理解和彼此约束的公平状态。
笔者认为,沙特作为一个现代世界中最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其王室成员在近年发起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行动,都恰如其分地印证了上述所谈及的三个重要事实:(1)沙特致富的道路本来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其石油的开发和国际交易只是少数王室成员内部对国民资源进行占有、交易、分配、获利的经济行为,权贵阶层把社会财富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他们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完全脱离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民主法治模式。(2)鉴于目前的沙特政治社会情况,仍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在阻碍着沙特的现代化之路,而它对伊斯兰教的神权政治体系的依赖,无疑是其诸多阻碍现代化的因素中最突出的一个。(3)最后,即便是沙特相对平稳地进行了现代化变革,那些已经被长期实践的旧制度的传统习俗、深入血脉的伊斯兰教义,以及残留自旧世界的封建政治势力和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都会有形无形中继续塑造和影响未来沙特的民间舆论风气和普遍社会共识。
四、
“强国”之路的道德挑战
在近几百年的中东历史中,沙特只是一个沙漠部落之国,长期以来隔绝于其他主流文明,保持着相当神秘和孤立的姿态。当今的沙特王室曾经也只是众多中东小部落中的一个。在1902年到1927年之间,王室通过一系列战争逐渐征服了周围的其他部落,终于在1930年以自己的姓氏来命名的沙特阿拉伯王国,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Aziz bin Saud,西方世界称其为“伊本·沙特”)成为其首位国王。随后,原本经济脆弱和物资贫瘠的沙特王国,在1938年勘测其到境内哈萨绿洲存有惊人的石油储备量后,从此一改仅仅依靠军事力统一国家的局面。二战之后,沙特与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签订双边合作协议,通过与美国至今不断的合作,一举跨上世界历史舞台,凭借自己的石油资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小觑的力量。
然而,现代沙特王国仍然难逃极端保守的瓦哈比势力对其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制约。沙特王室武力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离不开代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瓦哈比教派的功劳,而这一原教旨主义教派的势力也通过1979年武装占领麦加大清真寺的恶性事件,悲剧性地强行将沙特从现代国家管理和发展的道路拖了回来。可以说,沙特的现代化之路,既面临着本国内部复杂的军事、宗教、政治势力的“硬”博弈,又面临着传统思想和宗教习俗本身转向现代世俗人权理念的“软”困境,可谓前途未卜,难以预测。
相比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中所经历过的深入社会底层的启蒙思想运动,沙特王国的近代历史没有经过近现代思想的系统洗礼。其社会所长期依赖的伊斯兰教义,也远远没有做好和现代接轨的准备。其爆发式的经济富庶方式,没有得到与之相配套的精神文明发展:社会公正、法律建制、民主代议、民权保障和公权力的问责体系等等各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都未能落地生根。这种“单腿式”的行走,无论经济上如何强大,都无法令外界世界对其心悦诚服。无怪乎,沙特王国也只能是在国际社会中遭人诟病的落后世界或发展中国家代言人。
我们不是在否认沙特的富裕,但是,也没有人可以否认她的富裕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由此面对着不可持续的危机。但是,我们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是:即使是一个国家具备了可持续的经济繁荣条件,实现了强国之梦,为什么她也未必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认可?
笔者想要强调的是,从人类的历史事实来看,评价一个国家或朝代是否真正配的上“强大”之称的,从来都不仅仅是经济繁荣和疆域辽阔这两个标准。满足这两点的国家王朝,也许能被称得上是“强国”,却未必能被称得上是“大国”。即使是任何自称“盛世”的朝代,也必然会诉诸自身的道德优越性——所谓“国泰民安”,必须包括人民的安居乐业、轻徭薄赋,权力机构的政治清明、广开言路,而绝非少数官僚阶层鱼肉百姓、闭目塞听。
放眼国际政治,此情此理也同样成立。一个国家在地缘上的谈判优势——无论是来自地理和自然,还是科学和技术,还是经济和政治——和由此带来的“事实上的”强大话语权,并不是衡量她是否配得上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强大”的全部标准。事实判断之上,还有道德审判。所谓的真正的强大,既离不开外在的物质力量,又离不开内在的道德合法性,两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一个国家有了核弹,她也未必能赢国际社会的尊重,而有些地方虽是弹丸之地、人口有限,却也能被举世公认为强大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原因了!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一个无视现代政治规则、剥夺本国人民权利而因此缺乏道德合法性的超级强国,仍然会在国际舞台上被当做异端,无法获得她所企望的尊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虽然永远不会过时,却永远不会真正赢得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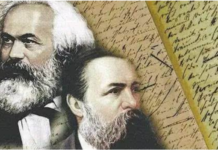
 《田纳西新闻》在建报之初一度是是田纳西州唯一的华文周报,总发行量最高超过一万份。近年来,《田纳西新闻》改为以网络为主,打造了《田纳西华人世界》微信平台, 继续为广大华人服务。本报以公平, 正义, 和平, 友爱为原则, 不带任何种族, 宗教, 政治偏见,竭诚为本地华人提供美国和当地的时事新闻和文化咨询。我们欢迎各类广告,有意者请拨打电话(615)977-8582。
《田纳西新闻》在建报之初一度是是田纳西州唯一的华文周报,总发行量最高超过一万份。近年来,《田纳西新闻》改为以网络为主,打造了《田纳西华人世界》微信平台, 继续为广大华人服务。本报以公平, 正义, 和平, 友爱为原则, 不带任何种族, 宗教, 政治偏见,竭诚为本地华人提供美国和当地的时事新闻和文化咨询。我们欢迎各类广告,有意者请拨打电话(615)977-8582。
